这个世界最坚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,朝鲜,在既要培养它的世袭者,又不得不让他张眼看世界的时候,选择了瑞士。就像,世界无数隐秘的黄金,也同时流向了班霍夫大街下的金库。这使苏黎世成为一个隐秘的存在。存在在某种传说中,存在在某些臆想里,在欧洲心脏的这座小城,于是拥有了无限开阔的外延。然而值得庆幸的是,它终归是个小城。它自然地依托山脉,依偎它唯一可称大气的苏黎世湖,沉默自然,富裕不言。
有几次我在旅途劳顿中一睁开眼,明明不相干的城市,眼前却突然浮现了苏黎世。从那个城市的火车站步行而出,仅仅几步,就能望见不高的山路在前,沿着山路一直走,可以走到著名的一所旅游大学。那里因拥有爱因斯坦和二十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,因此一直被视为高等教育的标杆。这是苏黎世的特点,质量和厚度足够,然而绝不会让你觉得太过辽阔而困顿。使习惯了快速扩张和地域广大、城市无边无沿的我们,难免而生弹丸之地的感觉。
这是一种交加着复杂情绪的感觉,你轻视其小?然而你无比羡慕其自然亲民和宜居。而且你根本不能忽略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。在无边无沿的城市里穿梭的我们,亲眼看见城市像一个怪兽一般膨胀的我们,每天都在探讨这城市如何作为我们合理存在和发展的我们,总是希望能够设定一种相对理想的城市生活。
苏黎世,是或者不是?如果不是,为什么会屡屡被称为“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”,如果是,为什么从苏黎世出发的航班上,经常会听见有年轻人在抱怨他们的枯燥和乏味?
是啊,年轻人难免觉得不被满足,从晚上十点开始,最热闹的街区班霍夫大街都开始显得灯光寥落。电车上寥寥无几的数人,似乎也在匆匆返家。夜游的异乡人此时定然发觉自己是个异乡人,尽管一个不大的城市易于给人一种安全感和错觉。仿佛这里才该是故乡。
在我们快速膨胀的城市扩张过程中,苏黎世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在离班霍夫大街不到一公里的某个山肩,我坐下来,看着下午的阳光带着一种像隔了二十年感觉一样的落下来。所有的人几乎都聚在河边或山上,随便啃一两个三明治,享受下午的阳光。只有在某个时候,一个穿着大衣的老年男子,抽着雪茄,以一个标准的银行家的姿态在打电话时,才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金融中心。只是你会问,为什么金融中心没有伤害掉质朴的生存。
在苏黎世,你最大的感受就是,一种连续性的生活,是怎样造就了安然和自如。此地古时并不平静,然而从两百多年前开始就不曾再有战乱或中断。传统的工匠意识,以及银行家的本能,使得苏黎世人精于算计,不断累积,同时固守乡土。像是某种独特的动物,将触角伸向了无穷远,但是身体却继续接受着滋养。
被“最宜居的城市”所蛊惑的人们,来了苏黎世,一定会杂糅着不虚此行和暗暗的失落。这里不是巴黎、米兰或纽约,这里是一座微茫之城。苏黎世在德文中有水乡之意。也许水乡历来都富足而宁静,只是苏黎世,因为在远远的少女峰下,更多了一种微茫和澄净的意蕴。
微茫总是和星辰联系在一起,仿佛星辰隐约微茫,瑞士苏黎世就像是天边的一颗星,它说着另一个故事,对于我们而言,这个世界还是显得和我们已经熟知的有那么些差别。它那么安静,那么自然,以至于我回想起它的时候,老觉得像是隔着二十年的阳光在看它。这是一座微茫之城,和我们快速膨胀的现实隔得如此遥远。
欧洲的安宁和富足,不间断的承续和发展,其实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全球秩序之上的,全球的血脉供养着一种理想的生活风格和状态。更人性,更自如的。这种状态可以被用来和我们参照并反思,但是显然人们不能抱过高的指望,因为全球的血脉供养不了太多这样的理想之城。









 瑞士奢侈品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...
瑞士奢侈品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... 瑞士SEG趣味探险
瑞士SEG趣味探险 全球酒店管理大学排名Top10
全球酒店管理大学排名Top10 立思辰留学携手瑞士各大名校 ...
立思辰留学携手瑞士各大名校 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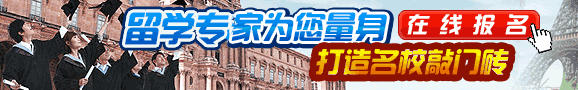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 SHMS瑞士酒店管理大学
SHMS瑞士酒店管理大学 恺撒里兹酒店管理大学
恺撒里兹酒店管理大学 瑞士蒙特勒酒店工商管理大学
瑞士蒙特勒酒店工商管理大学 瑞士库林那美食艺术管理大学
瑞士库林那美食艺术管理大学 洛桑酒店管理学院
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格里昂酒店管理学院
格里昂酒店管理学院

